清流文化指被“清流”(喻指德行高洁负有名望的士大夫)这个特殊群体所认同的一种政治文化价值系统和实践活动。
从8世纪中叶开始形成的清流文化,经过德、宪两朝君主的有意识推动,至9世纪中叶以后,俨然已经成为唐代政治文化的主旋律,特别是在宣宗和懿宗等朝达到巅峰。
这一文化的辐射力无远弗届,通过各种渠道影响了当时社会上层的心态和价值观,也左右了朝廷政治集团的用人抉择。这种发展最突出的结果,首先是前面提到的一种特殊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精英(清流)的出现;其次是大大强化了以宫廷为中心的文化想象。
尽管9世纪唐廷对帝国的实际控制力在减弱,以大明宫为中心的文化想象却反而呈现上升的趋势。通过文辞来为唐廷服务依然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中唐以后的诗作里,对进入禁中成为翰林学士表示钦羡的文字很多,这里只举其中两例,杨巨源《张郎中段员外初直翰林报寄长句》:
秋空如练瑞云明,天上人间莫问程。丹凤词头供二妙,金銮殿角直三清。方瞻北极临星月,犹向南班滞姓名。启沃朝朝深禁里,香炉烟外是公卿。(《全唐诗》卷三三三,1686页。)
咸通四年李频祝贺和他同年及第的翰林学士李瓒获得知制诰衔:
仙禁何人蹑近踪,孔门先选得真龙。别居云路抛三省,专掌天书在九重。五色毫挥成涣汗,百寮班下独从容。芳年贵盛谁为比,郁郁青青岳顶松。(《全唐诗》卷五八七,6811页。)
这些诗句充满了宗教性的比喻,将大明宫这一物质空间转化为至高无上的精神空间。即便在唐廷风雨飘摇的天复元年(901),担任翰林学士的韩偓作了《锡宴日作》,诗中捕捉的种种宫禁意象,表达的依然是一种身居人间天上的雍容和自在:
是岁大稔,内出金币赐百官,充观稼宴。学士院别赐越绫百匹,委京局勾当,后宰相一日宴于兴化亭。
玉衔花马踏香(一作天)街,诏遣追欢绮席开。中使押从天上去,(是日,在外四学士排门齐入,同进状辞赴宴所晚唐,奉宣差学士院使二人押去。)外人知自日边来。臣心净比漪涟水,圣泽深于潋滟杯。才有异恩颁稷契,已将优礼及邹枚。清商适(一作迥)向梨园降,妙妓新行峡雨回。不敢通宵离禁直,晚乘残醉入银台。(当直学士二人。至晚,学士院使二人却押入直,余四人在外,可以卜夜。内臣去外,知熟间丞郎给舍多来突宴。余是日当直,故有是句。)(陈继龙注《韩偓诗注》,15页。)
但这一文化对晚唐五代社会的最根本的作用在于,通过其影响力的逐渐扩散和渗透,清流的价值观即便在唐代朝廷权威实际受到挑战的情况下,仍旧显示出强大的霸权,使得这一群体的重要成员能在世变中维持其特殊地位。
9世纪期间,经由唐宪宗到宣宗等几代君主的努力,除河北以外的绝大多数藩镇已逐渐为朝廷直接委派的文官节度使或观察使所支配,这种情况从大中初到咸通末尤为明显。这些高级文官很多属于清流文化的代表。随着这一结构性的变化,许多节镇形成了以文官节度使为核心的文官群体。这一群体中最受瞩目的成员既来自于科举仕宦皆成功的文学宦族,也是日后进入中央担任词臣等清官要职的重要来源。

开元二十五年,李白移家东鲁,与山东名士孔巢文、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在州的徂徕山竹溪隐居,世人皆称他们为“竹溪六逸”。
清流文化和唐代后期的藩镇体制的结合是清流价值系统扩散的一个重要步骤。因此除了代朝廷立言的草诏活动,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实践就是霸府掌书记的工作。吴丽娱的研究表明,以表状笺启为主要内容的文集大量出现,就是中晚唐特有的现象。比如现存的李商隐的《樊南甲乙集》、刘邺的《甘棠集》和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等等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这种书写的功能,并非只是应付行政的需要,更是一种通过文字来与朝廷沟通或维系情感的重要礼仪性手段,有不可低估的象征意义和作用,因此文辞的斟酌不能只是达意而已,而是要在准确拿捏表法分寸的基础上说服或打动对方。
除了撰写章表这类活动使得藩镇需要清流人士之外,节度使府的举荐、公宴和酬唱等形式也使这一群体的个人关系更趋紧密,传达出来的趣味和长安的主流文化没有差别,可说是清流文化在地方上的再现。清流文化的影响力不仅在为文官所主导的藩镇内产生效应,还在唐末渗透到了长期为武人所掌控的河北藩镇之中。几乎同一时间内,从易定的王处直和王都,到成德的王镕和魏博的罗绍威,都以重视文士和喜爱图书文学为尚。
《旧五代史·罗绍威传》:
绍威形貌魁伟,有英杰气,攻笔札晚唐,晓音律。性复精悍明敏,服膺儒术,明达吏理。好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每歌酒宴会,与宾佐赋诗,颇有情致。(按:《太平广记》引《罗绍威传》云:当时藩牧之中,最获文章之誉。每命幕客作四方书檄,小不称意,坏裂抵弃,自擘笺起草,下笔成文,虽无藻丽之风,幕客多所不及。[《旧五代史考异》])江东人罗隐者,佐钱镠军幕,有诗名于天下。绍威遣使赂遗,叙南巷之敬,隐乃聚其所为诗投寄之。绍威酷嗜其作,因目己之所为曰《偷江东集》,至今邺中人士讽咏之。绍威尝有公诗云:“帘前淡泊云头日,座上萧骚雨脚风。”虽深于诗者,亦所叹伏。(《旧五代史》卷一四,191页。)
笔者认为,晚近出土的唐末五代交替时期的易定节度使王处直墓的图像系统也是体现这类清流文化价值观渗透到河北职业武人群体中的一个显例。
以往研究者往往依据宋代的儒家舆论,强调晚唐五代是个以武力为霸权的时代,而北宋的统治精英有意识地在价值观上远离五代的政权意识。这种强调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唐末五代固然是个纷乱的时代,普通士人受到的待遇的确不如晚唐承平时代,然而在这一表象之下,晚唐清流文化的力量并未有实质性的减弱,相反,这一价值系统及其所依托的制度、人员以及社会想象都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沉着而有序地在五代十国的政权中成长,至少确保了在社会的最上层文武两种力量的某种均衡,为奠定北宋初年的政治文化格局起了关键作用。
唐末清流文化的代表人物,这些人物的子弟,以及唐末从这个文化系统里产生出来的新成员,在五代十国的许多政权里都纷纷占据了显要的位置。关于唐末翰林学士群体在唐亡之际的际遇,傅璇琮在《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中有精细的考释。
这些政权,无论南北,通过吸纳这些成员而获取政治文化的资本。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
梁李相国琪,唐末以文学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迁,衣冠荡析,因与弘农杨玢藏迹于荆、楚间。杨即溯蜀,琪相盘桓于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迹,号“华原李长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尝厌薄之。琪相寂寞,每临流跂石,摘树叶而试草制词,吁嗟怏怅,而投于水中。梁祖受禅,征入拜翰林学士,寻登廊庙。(《北梦琐言》卷六,贾二强点校,143页。)
这则例子形象无比地说明李琪这样的中朝子弟在落难之际,感叹的竟然是自己草制之才的无处发挥,以至于不得不通过在树叶上拟诏来过干瘾。直至得到朱温赏识,才一偿夙愿。孙国栋认为,五代十国政权对文士的优礼,“仅限于文辞秀句,以掌书檄而已,于儒行无与焉”(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289页。)
孙国栋的这段评论是对《旧五代史·李袭吉传》传末评论的引申,该传只指出唐末藩镇争用一流书记人才,而孙国栋的评论则认为这并非对文化的全面支持,而是某种狭隘的需求。笔者觉得他恰恰忽略了这一现象的真正意义。可见他注意到了这个特出的现象,只是他的理解并不准确。
为何在一个武人力量空前强大的时代,却如此急迫地需求能书写精妙的以骈俪文体为主的文字的人才呢,而且给予如此礼遇呢?这绝不是出于一般意义上的沟通的需要,而是一种特殊的沟通方式,这种方式是以整个沟通的网络都接受了某一种政治文化价值系统为前提,也就是说,从正在衰灭中的唐代政权,到各种争夺政治权威的力量,都认为掌握能书写这种文字的人士对于政权合法性和政治形象的建立都有关键的意义,而且也相信只有通过这种手段,才能与对手或政治联盟进行深入沟通。没有那样一种政治和文化的想象,这种追求文辞秀句的书檄的现象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唐末涌现出来的有刀尺之才的文士被地方政权重用,成为代言人,这类人才反过来成为清流代表的庇护人。
现代的研究者间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五代十国政权用唐朝旧臣和名家子,只是为了要利用唐朝的政治资源。这一看法比较片面,唐朝旧臣的类型很多,为何偏偏是某一类旧臣特别受到重视呢?而所谓名家子更是特指有科举和词臣背景的官僚家族后代。除了延用这些成员之外,五代十国政权还吸纳没有这些背景的新出文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人的特点和进入新政权之后的生涯轨迹,与晚唐的清流十分相似,文辞瞻博敏速往往是最突出的条件。
晚唐的清流文化,在五代之时得以延续依靠的还不仅仅是其成员的仕进和科举等机制。其成员通过有目的的回忆性书写,在历史记忆中不断对这种文化的细节加以建构和渲染,看来也曾起到相当的作用。现存不少唐末五代的笔记,从裴廷裕的《东观奏记》、令狐澄的《贞陵遗事》、孙棨的《北里志》、康骈的《剧谈录》、尉迟偓的《中朝故事》、王定保的《唐摭言》、阙名《玉泉子》、高彦休的《阙史》、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和刘崇远的《金华子》等等,都与这种努力有直接的关系。这些笔记的存留,固然有偶然因素,但其作者中具有词臣身份的比重颇大,却也绝非偶然。唐代清流文化最为重要的制度依托是进士科,而保存这方面资料最多的《唐摭言》,恰恰出自服务于南汉政权的王定保之手。有意思的是,在对晚唐五代清流代表人物的评价方面,这些笔记的趣味和立场往往和官修的《旧五代史》相当一致,而和欧阳修等撰的《新五代史》大相径庭。
唐后期形成的清流文化的特点不仅仅是已经拥有清流身份的人物及其家族对政治和文化话语权的垄断,同时也具有不断生产新成员及其家族的机制,只是这种生产是遵循这一文化所强调的模式来展开的。这种复制机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接受其价值观的社会想象的存在。当然五代十国时期,在复制这种文化及其代表人物时,随着历史境况的改变和人物背景的不同,种种新的变化也自然会以各种形式崭露,对晚唐以来的主流政治文化做出不同程度的改造甚至拒斥。清流文化余波下出现的新代表人物,他们的政治生涯固然得益于这一文化,他们家族延续这种成功的能力则很可能不断下降。但正由于唐末的大乱和清流文化取得霸权地位这两种现象同时出现,认同这一新政治文化的大量一流文士才能在远为宽广的空间范围内产生影响,这是唐代衰亡最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
作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文化模式,清流文化究竟何时才明显不再处于历史舞台的中央了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过也已经超出了本文既定的讨论范围和笔者的学识。但基于非常初步的考察,笔者倒愿意提供一些粗浅的看法。清流文化与北宋新政治规范的建立之间恐怕存在着相当深刻的联系,这一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在北宋的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依然清晰可见,无论朝廷对文臣的选择还是重要文臣的仕进模式、文化旨趣(从文学风格到宗教实践)和社会网络的构成都提供了很多证据,具体的情况需要另外撰文分析。
士大夫对于清流文化的评价,在长达四十多年的仁宗一朝终于出现了明确的转向,曾经被视为超越政权而存在的那种维系政治文化的力量,开始沦为道德谴责的对象,相关的历史记忆也随着宋儒的努力改写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这个变化说明这一曾经以宫廷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模式,虽然在北宋初期仍然拥有话语权,已越来越面临来自不同背景的文化精英的挑战。以欧阳修等人为代表的新知识群体也许曾与晚唐以来的清流文化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却无须在心理上再对之抱有以往的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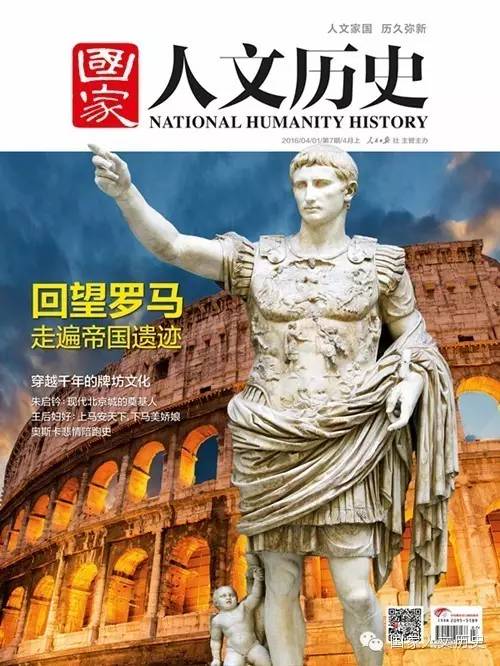
新一波古建游来了!
“醉美古中国”乡旅活动将带您,深入江南古镇,赏木雕,游乡村,享受恬淡宁静,放慢脚步,找寻生活本来的模样……感兴趣的朋友,长按图片,了解详情。
限时特惠: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展厅资源,一年会员只需29.9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站长微信:zhanting688





